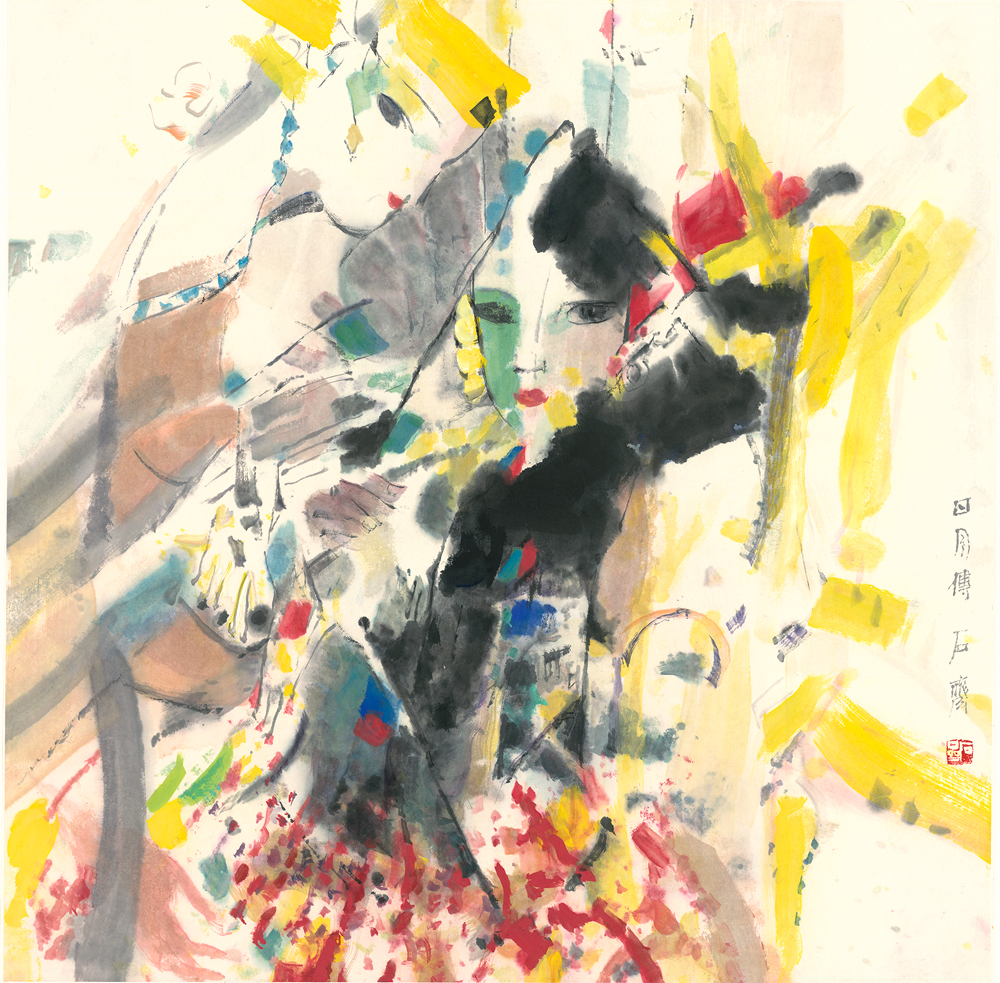题记:2006年3月27日,我和《中国水墨》杂志的编辑项堃、王怡一起到石齐先生家中,与他进行一个对话。傍晚5:30分,我们准时到了石齐先生家里,一进门是一个大的书架,上面只放着石齐先生自己的画册,没有其他的书。进门后,宽敞的画室中挂着他的作品,有的完成,有的未完成,几件旧式家具摆在客厅的中央。我和石齐先生此前没有见过面,对我并不熟悉,我也没有多说什么。也许正因为比较生疏的原因,所以没有过多的客套。大家坐定,由我先来发问,石齐先生做答,就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刘墨:昨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经常喜欢用“进步”和“退步”这么两组词,但是你能告诉我100年来的中国文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石齐:退步了,文化的退步啊。
刘墨: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比较关注一个问题,即一个人文学者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教育的背景问题。自然,当我研究一个画家时,也会比较关注画家成长及其教育背景的问题。这个教育背景问题,有许多提问及访谈者恐怕并不大去关注,因为大家都处于一个基本相同的教育背景之中,在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之下,所遇到的问题情境也就差不太多。如果我们有意地拉开一些距离,跳开一下,比如说,您这一代画家和上一代甚至黄宾虹他们那一代画家比起,就能看出您与他们的教育背景的不同之处。因为我觉得,教育背景对一个踏入艺术之途和踏入之后的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师灌输给他的或课本灌输给他的,以及他自己所能见到的,都会影响到他会寻求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因而会决定他以后的艺术道路,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先从您的教育背景来谈一下。
石齐:对于我们这个年段的人来说,教育背景直接受社会影响多一点。大家也比较愚钝,听一个人怎么说就怎么做。老是受外在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也比较倾向画画,立志做一个画家。十岁的时候就在全校画画比赛中夺得第一名,被人称为“小画家”。这也是一种动力吧,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画家。当时的社会背景比较不同,你想成为什么“家”就是只“专”不“红”。我戴这个帽子起码戴到“四人帮”倒台很久以后,一直戴到我到北京画院成为一个专业的画家,领导还在提“专”有余而什么不够、年终总结时还提认错不够。我曾想,我是不是一辈子就只能让人扣帽子了,成为专业画家还让人扣。你就是很用功画画,政治上不够它也得扣。所以从小一直到专业队伍里很长时间,心里很茫然,甚至有些恐惧,因为戴这个帽子,心里想一定要成为画家,而且要成为出色的画家。这股力量抵制了很多外来的压力,那不是一方面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因为我原先是搞工艺美术的,也画油画、水彩、雕塑、版画等很多专职,什么刺绣啦都得干。因为工艺美术嘛,像装潢广告啊都得干。但干这些我依然想成为画家,人一定得这样。然后就是学校毕业后作为做工艺美术工作者而被分配到北京来了,不是作为画家被分配北京来,跟美院不同,美院分配北京来是以画家身份,我分配北京来是搞装潢设计,到一个装潢研究所搞装潢设计。那么我来北京一看呢,也是这样。就比“红”,根本不讲“专”,这是一个社会背景。单位也是这样,你只许“红”不许“专”,你要“专”就搞你的设计,我又特别不喜欢搞设计。
刘墨:一直就想当画家吗?
石齐:是的,我就想当画家。所以呢,如果让我搞设计也能搞好,但我不想搞,我就搞中等性,把握中等性,领导给我任务能完成就行了,我把握着这一点。太差肯定天天还得受批评。我业余时间就画画。当年讲出身,我出身比较好,他不敢把我怎么样。但劳动的事都是我,什么上山种树呀,什么民兵训练啊,
所有外面的政治这些事,都是我来干。因为我爱画画,周围同志向领导反映说我不“红”,所以我怎么个搞好、怎么个学雷锋、怎么样单位搞得多么好,从学校开始,人们都认为我是假的,我有目的,还想掩盖我只“专”不“红”。这个很可悲。我们想学雷锋,以雷锋为模范,为人民呀,我一感动就想学这个,人家放假回家 ,我呢不能回家,在学校干点公益的事,种种白薯呀,但从未得到过表扬。
刘墨:那在您受教育的过程中,来自于文化艺术方面是比较少的。
石齐:很少,来到北京之后,也就是我靠业余时间,中午时间、晚饭时间,还有礼拜天到故宫去看一些中国的绘画,到那临摹去。常去临摹,在星期天,还得悄悄的,不要被别人发现。
刘墨:那现在比您那个时代要好得多了。
石齐:多得多。
刘墨:但是在现在,仍然会有很多人批评现在实行的美术教育制度,比较成为焦点的,是研究生的考试制度以及培养方法等等,您对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有什么看法呢?
石齐:就我本身以为,像我们书画艺术方面,你想如果你有天才,不注意那些基本的功课,甚至英语,就想破格录取,那不会的,极个别人不会代替教育制度的改变。所以就是有人在电视里头慷慨激昂地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教育制度是个整体的事,我们一切都要服从整体,你说你是天才音乐家,是有三岁
多就可以弹得很好的,难道他不需要基本功吗?不需要英语吗?这个用不着讲,必须严格。因为你必须语文要好,理科要好,政治要好。如果我是老师,我依然严格要求,我还嫌之不够。不过我有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给教育上多一些优惠,国家要出钱。这点做不好,就会使穷人、有智慧的人上不了学。再加上经济的大潮流,很多工农子女,孩子的父母不要孩子上什么大学,帮他们嫌钱。觉得花那么多钱十万、八万、几十万上大学、送他们到外国留学,到头来还是回来,花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别干这事。所以他们有这个错觉,一方面想让子女做大学生、留学生,什么都想,一方面又不想让他们上。
刘墨:的确如此,因为在我看来,把担负教育责任的学校产业化、把教育行业产业化,也就是把学生当做了商品,同时也推卸了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过,我更为担忧的是,现在的大学教育,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切断,也就是与自己国家民族文化传统历史脱节,或者背道而驰。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教一个人如何成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它把教育分成内外两面,知识技能在外,心情德性在内,内部的心性德性,更重要过外面的知识技能,否则就不能归入人生境界。现在的教育,显然于此注意不够。
石齐:我还听说一个学校,比如说什么大学、什么学院,你本来是学院,你应该是科室应该是系,为了赶潮流把系也变成学院,外国人来采访,院长介绍这个院长、那个院长,他就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这这么多院长,实际上还是一个院,华而不实,弄虚作假。你本来是一个系的能力,偏要说成院。本来是一个学院,马上变成一个大学,你哪有那么多资金?有那么多师资力量吗?都没有,一切都没有。既然不到位,就不要那样去干。所以我呢虽然是一个画家,不是教育界里头的人,倒不是反对慷慨激昂地去说一个人没才干,他怎么不要学英语不要学什么,别的学科松一点。这是少数人,少数人怎么能顾得起来!国家不能把整个教育体制为了个别人而改变。
刘墨:我觉得您这个声音是很重要的,现在确实也很难听到说这些不同的声音了。但是在实际上,对人文学者或教育学者来说,他们对这些问题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他们可能不愿意把这个声音表达出来。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研究生制度的设立,本非为了美术,我们无法想象学习哲学、文学、历史、物理、化学、数学的人不懂外语。从某个角度来说,美术确实可能不需要外语,但是学好一门语言,等于多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所以它还是非常重要的。您的教育背景,就像您所讲的,更多地受了外在因素的影响,于是您在学习和认识文化和艺术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多干扰。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来自于西方的因素,比如说您对于色彩的看法、对于形体的看法、对于结构的看法,这些因素在传统绘画里面就少一些,而在西方绘画里就多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对西方是如何认识的?
石齐:这个说开来范围很大。因为作为我们中国画来说,它是小农经济艺术,它只是一种被文人用来消遣、称之为雅兴的艺术。画画的只能在很暗的房间里头,也不能在宽阔的地方。多是文人聚会,你一盅我一盅在一个大的官宦家中。有的在宫廷里,形成宫廷画。但像西方艺术那样有一个宏大的空间、一个全面的视觉,我们都没有。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小而灰暗的空间里头,甚至看一张画都要用放大镜去看。这样的做法,我们哪有视觉?一是视觉不够,你说有作壁画的,是富丽堂皇的,可那是一时,并不是全部。西方那是全部都在,大空间、大视觉。
刘墨:建筑当然很重要,西方艺术史就是从建筑艺术先说起,有了建筑之后,再有雕塑,再有绘画……
石齐:是啊,人家大视觉、大空间。我们呢?我有回在黄胄老师家里,看黄胄、启功等人凑在一张条桌上看一幅仇英的画,他们抢着一个放大镜鉴赏那幅画。启功说:“黄胄你看,你看他这个眼睛,画得多活?”
其实才芝麻大的一个人头,他就激动:“你看他眼睛画得多好,那笔触、那鼻子、那嘴、那角度!”放大镜看的。那么小的一张画就那么激动,抢着放大镜看。我当时就想,坏了,我们中国画坏了。我们不能这么干。抓一把蚕豆、一把花生米搁嘴里,喝着酒你说一句我说句闲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中国画需要大视觉大空间。我当时就想,不是今天是十几年前,中国画需要近距离看里面一笔一笔是怎么画的,错了!大大错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画画都是一笔笔去勾,整个视觉觉得一片不堪。一看这怎么黑乎乎一团尤其是山水画,全部都塞满了。人物画就画素描,水墨画画素描画,它居然显着局部笔墨。西方大框架、大视觉的问题,你是一比就差的。你只去追求笔墨,那么百姓能懂吗?根本也不懂,那谁懂?西方懂吗?人家也不懂。西方是科技的发达、工业的发展,人们渴望生活水准的提高,渴望更高一层,更具冲击力。因此我们拿画去西方展览,他们就拿老祖宗那么一点东西来展览。你即使个人有点视觉他也看不上,你搁在那儿跟我有太大差距,我也不愿你跟我挨着。不是说中国画在国外展览很受欢迎,并不。我们也出去,还不知道吗?人们因为中国画太缺少冲击力了,它就和那时空隔了一百年!一百年哪!还不是一天两天!挺可悲的一点。离我们政治改革也很远。事实上应该是,文化艺术走在前面,政治、制度改革走在后面。你想人家提倡制度要改革,国家要改革,你还在涂这小笔小墨,用放大镜去看一个局部的笔墨,多么可笑的一件事。还自以为是,还会说你不懂,你嫌弃它还说你不懂。这就是现实现象,你怎么办?那很不好啊,同行都很好啊,各干各的吧。
刘墨:从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走进现代的前提,一定要把传统的东西抛在脑后才行,或者说,现代化的前提,必须要抛弃传统。您吸收了西方的影响,西方有没有评论家对您的绘画做出过一些评价?他们怎么看?
石齐:真正西方人很少看到中国画,都是那些华人。我们说的话可能也片面。我去一个国家也去看看当地的华人街。我们的华人兄弟他们生意做得很好,也把中国文化带过去,但不是带着精华而是带着糟粕去,带着封建迷信去了,什么关公啊,什么大佛爷啊。
刘墨:不过也有不同的现象。比如我认识的或我所知道的人,他们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是很向往西方的,对西方的艺术文化非常推崇,因为他们在国内时几乎不大容易见得到真正好的中国艺术品。可是到了美国去以后,比如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他们去中国馆看中国艺术品的时候,确实是被吓了一跳。那么在这个时候,非常狂热的向往西方的热情,就在像您说的这种很内向的、很冷静的中国艺术品的面前,他们感觉很震惊,所以从那之后,有很多人变成国粹派,开始相信中国的艺术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是非常好的,这个态度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您概括得很肯定,就是西方绘画有一个大视觉、大形式,这个是它优长,但是呢,您对于传统绘画——就像品味的、细腻的、微妙的,甚至是这种色调很灰暗的,您觉得这些与西方相比,如果说不是缺点的话,也可以说它是比较弱的一个方面,那么当您这么来看中国绘画的时候,比如说您对中国绘画的品评,就和黄胄、启功他们那一代人就不一样,所以有这样的差距,您是不是觉得有教育背景的因素在里边?
石齐:应该是。说得很正确,应该是。启功、黄胄特别是刘海粟,这几位老师,尽管也到过国外去,像留法呀等等,回来带来的艺术观点对中国绘画界也有推动,但依然没有很好说出西方绘画的优点何在、中国绘画的优点何在。没说清楚。所以我那回,就是两三年前在清华大学讲的一次课——题目就是《传统中国画的先进性何在?》,就谈这个。
刘墨:刚好,您现在说的和我想要问您的下一个问题连在一起了,您是如何认识传统中国画的?
石齐:我当时提出“先进性”,不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啊,它在我这个后头,不是我抄它的,它也不可能抄我的,人家是国家嘛。(笑)我是说不要误会我说的“先进性”是利用政治来做文章,我比它早,也不是跟国家比啊。国家是多么伟大、个人总是渺小的,怎么能放在一起比呢。这个传统绘画有大优点,而且是西方不能代替的一点,就是我们从生产习惯、从艺术技巧上跟西方不完全一样。这个是很伟大的一点。人们把艺术形式分成“两象”,我说是“三象”,不止“两象”,给它分“三象”比较合理一点。我在1981年提出,说西方艺术是“两象”的观点是片面的,不是抽象就是具象,我为什么说它片面?因为抽象的什么都看不出来,物体看不出来。毕加索的画什么都能看出来,如果把毕加索搁在印象派后期里头,那很合其理。对不对?现代人喜欢印象派,纯粹说具象还太早,抽象还不懂,这个阵容很大,而且代表人物一个比一个棒,非常出色。你把毕加索往抽象里面搁,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因为他的画很多人都知道,他画胳膊画眼睛,还来什么抽象?你刚才说波洛克,德库宁这帮可以算,还不错,不能乱分。
刘墨:其实,纯粹抽象的出现,是以康定斯基为标志。二战之后世界艺术的重心从纽约转到巴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出现,也才是真正的抽象。在此之前,虽然像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绘画里面有抽象的元素,严格说来,都不算抽象派。
石齐:对,你这个定下来是很对的,毕加索有名,人们一提到毕加索就是抽象派的代表,我坚决反对。所以我提出“三象”,哪个代表人物各占哪个时期,哪个时期代表什么非常准,不会乱。
刘墨:这个对于学过历史学的人,或者对历史学特别清楚的人,这个年代的人物,他就不会弄乱。
石齐:我们对于视觉是以东方人的欣赏角度去欣赏的,西方绘画的欣赏方式都是一样的,手法都一样。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绘画要比西方先进得多,怎么这么说呢?我们用线塑造形体,以现代眼光去看,这个依然是非常先进的。西方才刚刚开始要学着用钱来描绘一些东西,那就很有意思了,毕加索学一点点,马蒂斯学一点点,马上出效果。而我们因为在这个窝里一代代长大的,倒麻木了,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过时了。不对的,我从来不觉得是这样。优点就是优点,拿到现在依然是先进的,要发扬,不发扬多亏呀。我就跟他举西方用线不好用,因为画油画用的是画布,颜料像浆糊一样,粘乎乎的,不好勾线。我们中国画铺在纸上用墨来画,好家伙,怎么来勾就看自己。我们祖先的线,是单一路,细线都细线,我们现代人细线、粗线交替组成是线,断断续续的线组成也是线,用颜色不同的颜色勾成线,组成画,也是线,这在祖先时没做过,只有我们现代人敢做。西方人做不了,因为他是材料决定的。画的正面我们可以画,反面也可以画,西方人做不到。齐白石画虾米,为了顺手,翻过来画,翻过来看。他是为了顺手,而不理解这里头的长处。我们画画用的宣纸很薄,前面画很洇很不畅快,再翻过去就坏了,你再画翻面被它打湿了,就更模糊了。只有这样两面加工,能够弥补我们的缺点。西方很丰富,我们很单一,这点可以弥补。
刘墨:但是这种丰富和这种单一,或者叫单纯,它是属于美学上的概念,我觉得不应该说是丰富就好,单一就不好。
石齐:是这个意思。你认为单一了,你感觉单一了,朴素一点的东西、单一一点的,中国画它这个点线面呀,原来是交替的画。西方不主张,原来传统的西方油画它讲面,即便要组成一条线也是由面组成的。
刘墨:我小时学画画,看过一本书西方人写的书,叫《如何向大师学绘画》,第一篇就说,自然界是没有线的。
石齐:对,所以它觉得没有线。我们学油画也是这样,我们想勾一点线,老师就会给你涂掉,你的线要靠面组成。
刘墨:可是,早在唐代张彦远的时候,就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无线者非画也”,意思说得非常明白,没有线就不是画。
石齐:我们以现代角度去讲,没有线也是画,没有面也是,仅用线是画,仅用面也是画。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点吧。修拉用点组成一幅画,印象派的,如果我们也用点点成一幅画,那不是和修拉学了吗?没有多大意思。如果大点、小点、不同点组成应该是不错,你说是不是?就是单用点,你也别跟人家学。点夹杂点构成,夹杂点抽象,这点不就很珍异吗?
刘墨:其实早在17世纪时,石涛就在画论里以及画面上就有关点的各种技法以及如何用点来组成一个画面进行探讨,其论点是相当高明的。
石齐:噢,17世纪,那修拉还没有出生呢。
刘墨:修拉是二十世纪初期,差将近三百年呢。
石齐: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跟西方学,但如果不以我们的优点为基础的话,我们的中国画就没了。所以陈独秀也好,蔡元培也好,一直到后来的徐悲鸿他们,都有不同的革新,但效果甚微。这一百多年来,不明显,效果很差,这是由人文和历史决定的。中国画特别古老,越是古老越是有特点,越是有特点越保
守,这是规律。越有特点越保守,你不保守马上出错了,没了。所以他就很难过啊,现在我们也搞革新,也想再往前走。但你得小心一点,一不小心你就被融化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搞中国画创新,如同走在十字路口上,一不小心就成别的了,我有朋友很有名,人格也很高,但不是国画。所以我们中年很有成就的一批画家搞画展,几个人搞画展,搞的都很有特点,我很喜欢,可题目却是中国画,我说你别写“中国画”这三个字就好了,因为你们都很年轻。当时刚好这边是中国百年画展,那边是七个画家,后来我给他们评价,你这七个人的画展要比那个展览新,这个评价很高了,可是你一写“中国画”三字,很多挂出去不是中国画那怎么办?他们就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是批评还是骂。
刘墨:这点也可能和批评界的一些状况有关系。比如说去年在北大的时候,我与牛津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绘画和研究中西方美术交流的苏立文有一次会晤,跟他谈话的时候,我问他说:“现在的中国画和过去的中国画,以及抽象一些的现代派,你更喜欢哪一个?”他的说法是:“我不管是不是中国画,只要画的好,我就喜欢。”我想他代表着一种看法。
石齐:但是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有人问黄永玉说:“黄先生,您的画不太像中国画。”黄永玉讲:“我没说我的画是中国画,我只说说这是黄永玉的画。”人家这很公平的,你本来不是中国画还缠着挤到中国画的里面来,画中国画的人当然要挤你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冒充中国画。
刘墨:当您发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先进性,和它的特点或者它的长处,您能不能用概括的语言阐述一下这个传统的精髓是在什么地方?
石齐:传统的画非常好,精练一点说,是跟生活不太一样,画你这个人有一点像但不纯像。
刘墨:那就不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吗?
石齐:它非常考虑这一点。如果一个丝毫没有受过绘画教育的人去画老佛爷,去画罗汉,画它的相貌、注意它的笑,谁都能画出来,慢慢磨呗。有点感觉,但就是没有专业画。中国画是这样,油画不是这样,它要架起来,任何一个人慢慢看,看到什么画什么,但在动态情况下,尽管你多么有本事,动态都不行,这就是西方的画。但是西方的画一说到抽象,就很厉害的,很有感觉、很有色彩感,很有线条感,很有音乐感。从这一点说,我们就不能够说中国画要比西方什么画高明,多好。他们非常大的优点是他们“三象”一族,“三象”鼎立。抽象、具象、印象,都是一批大师级的。全世界你不能不说油画是给画里面的极致,因为他们三象一族。你看具象,多逼真都有,你看抽象,多抽象都有,你看印象,什么模样都有。我们呢?
刘墨:我做过中外艺术的比较,我的做法是,当我们做这种中西比较时,应该把第一流的作品拿出来,我们不能用最好的西方绘画和潘家园地摊上的国画比,同样也不能用我们大师级的作品去和国外的普通绘画去比。比如说“抽象”,像波洛克,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找一个八大山人的画,同样也给它放那么大篇幅,那么在幅面和色彩上面,或者说在精神的冲击力上面,我觉得八大山人的作品的包容量会更多。我还做过一个例子,莫奈八十岁去世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他画了许多睡莲,画很大。黄宾虹晚年白内障,也不大看得见,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但黄宾虹的幅面比较小,如果把黄宾虹的画在幅面上放大到同等的时候,那种视觉冲击力可能并不比壁画弱,而且它动人的力量会更多一些。还有一次,是我在南京博物院看徐渭的《杂花图卷》,他们搞了个局部放大,一块墨放大到一米五宽、三米高,我一进门,颇为震惊,太好了!
石齐:好,这个谁干的?现代人干的,不是徐渭他们干的。因为你有现代的思维,现代的渴望和要求去解答一部分优点。黄宾虹也是如此。我很喜欢。我有200多个学生,教他们学画。我说黄宾虹这个土坡画的好极了,别的地方平平,你还学他干什么?你作为后来者,哪有时间学这个啊,黄宾虹的画,桥梁不太好、人物不太好,三角线也不考究,你学他干什么?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把那一块拿出来加以放大,拿到原作上去比,肯定比原作好得多的多。这就对了,这是现代人,不是很离谱地去攀比。你为什么这样看啊,通过现代人的视觉要求切割了,达到好极了。人家西方却是本来就这么好,黄宾虹没有那个境界,他整天干什么?鉴定呀,几万张画让他鉴定,他就编辑,还代写语录,哪有时间啊?哪有这个心境啊?那土坡画的方位、意境很好,就是这种情况。作为后来的画家,我们缺少的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在你的画面出现就可以了,你是有效果,可他并不那么高兴。虽然从他身上出的东西,他并没有想的那么丰富,是你给他再创造了,这样说是不是比较公平一点?
刘墨:现在我们转到另一个问题。因为您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长处、短处都有了很清楚的认识,在您自己的创作当中,您肯定会反思传统里面的种种不足,或者是如何把那些好的东西留下来。这个出发点在什么地方?
石齐:中国画最迫切的要求,就是革新点在哪里,要求大气,具体要求是:线要加以扩大,无限扩大,面也要跟着来,点、线、面要加以扩大,不要呆在小房间里拿着小毛笔做、做、做!不行的,时代过去了。点、线、面是本土的东西,要加以扩大。不要去学人家,画一个人要画的特别真实,你怎么样也真实不过人家,人家上面可以改上一千遍一万遍,改十年。你改上一遍,第二遍就砸锅了,这不行啊。所以这个要避人家长,人家能画无限的像,我们这点不如人家,就不要硬强,硬强就没意思了。我们的优点在哪呀,
我们加以无限发挥,你不无限发挥,你跟着人家,自己的优点不发挥不就落下来了吗?你该发挥的不发挥,不该发挥的你玩命发挥,所有的个性都倒退了。比如徐悲鸿。新中国建立后,徐悲鸿很受重视,从国家领导到政府,整整五十个年啊,全世界任何一个画家都没有这样过。他的作品怎么样?你们分析吧,徐悲鸿把把西方造型融在中国画里面,中国画这种追求和效果,也有一定的时效,造型问题前进一大步,这是一大功劳,另外他本身画的也不错,当时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都以他作为榜样。可是再把他拿到二十一世纪作榜样,就已经不适应了,已经落伍了,人家会怎么说呢?因为他的笔墨充其量二流,他不是一流。他的笔墨跟吴昌硕无法比,无法比。我说什么意思?公平一点,不是说我们对徐悲鸿有恨,没有,我们分析一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嘛。我经常给同学们讲,扬州八怪有先进的一面,但是比较古,比较靠近现代,但是你们不要去学他们的笔墨,为什么?他们的笔墨并不高明,你学他的笔墨,还不如学李苦禅、吴昌硕、李可染,他们要比扬州八怪好得多。可是人家原来的先进性你又不能否定掉。
刘墨:您提到扬州八怪的先进性。扬州八怪绘画里面那种新,或者说某种新的元素,实际上和当时扬州发展的经济有关系。因为他们的买主面对的观众是这样要求的,如此说来,艺术和商业的关系,或者说商业有的时候会改变艺术的风格,某种艺术风格有的时候也会适应这种趋势,所以艺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
石齐:比如说任伯年这个人,有天分,用功,好学,人物画画的非常华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伯年画画又画的很油,也就是过于熟稔,缺乏进步追求,因为他依仗才干,所以他每幅样样珠圆玉润,都不错,人物画不错,山水画不错,非常有意思。这个任伯年玩命画,为什么,他抽鸦片,他不画哪来钱?所以他有个老板,老板是盐商,老板要画盐就画盐,要山脉就画山脉,什么时候要你完成你就得什么时候完
成,为了抽大烟啊。产品很多,就缺少时间考虑,他不像现代人,这张怎么样,那张怎么样,拿出一批画来,五十张画五十个样、几十个追求。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要求。
你说的经济的发展,跟绘画有直接联系,有的画家啊,画一种东西人们喜欢之后,就不想再搞这个创意了,还有一些画家非常有才气,尤其是美院毕业出来的。比如我先画具象,具象好卖啊,所以他要雇模特去家里,一个月,3000块啊,在家里画完了就拿走,我记得一个美院毕业的,说我们先弄房子、汽车,你想年纪轻的画艺也不高,那么要房子、汽车,那得画多少你不喜欢的画啊。
刘墨:看起来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在实际上,他在这个商品化的过程当中,他的品性也在变。我经常说,当一个人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他只要再坚持下去就可以了,因为他已经准备了相当的力量来度过这个难关,一度过去,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可偏偏许多人都是在这样的关口放弃了。
石齐: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刚开始他非常用功,不断地画,个子高、背有点驼,画素描,画西方大师的代表作,天天画,他妈说:“你别画了,你不是这个料。”他跟他妈生气,后来画出来了,画拿到美院去,美院都表扬,出了本画册,拿到国外去,很多专家都表扬,甚至克林顿都给他回信,因为素描人们都懂,不像国画懂的人不多。克林顿现在下野了,但是在朝的时候都由总统助理给他回信。经济浪潮一出来,就淹没了,他每次到我这来都说:“石老师,我这不甘心啊。”他是画家的材料,但对于做生意,他觉得不做可惜。做生意就没时间画画,后来我问他:“你马上快五十岁了,你什么时候再开始画画?”他说我还早,岁数不大,我说:“人家十几岁的画比你要好了。”他说:“我要挣到利息每年100万美元,我就不做生意了。”我就没话了,我说:“好,你慢慢去挣。”这样一个心态,他怎么能回来呢?所以这个经济潮流的确影响了一大批有成就的人、有天分的人,不是一个,好多都受影响。还有个从画院出去到国外的一个高材生,几
十年过去了,去时年轻,回来了变成老头,满脸皱纹,他说:“你看你在国内还是个画家,我在美国做女士雨伞把手上的雕塑。他就干这个。说起来为了谋生。这说明一个问题,生活、经济能改变一个有才干的人的命运。
刘墨:上一代人被政治影响改变,这一代人被商业、经济、世俗影响。这是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
石齐:还有,我听画家们说,一种人想画细点卖,一种人希望画简一点,本身不简,给它画怪怪的,也许有人买,你本身要怪怪的也情有可原,你本身是挺正的,你何必要弄那个呢?所以经济这个东西很厉害的。直接影响,不是一点点影响。
刘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问题会影响到现在人的心态。我今年40周岁,我小时候想找本书读不容易。现在呢,书太多了,你到书店什么书都有,所以学生问我该读什么书,书多的已经让人失去选择能力了。像您或者比您岁数再小一点的,他们长队排在新华书店门口,就是为了买一本新书,可是现在呢,你给学生列一大堆书目,他跑到书店去,要么全买回来,要么一本也不买,买了他也不看。
石齐: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的书太多。有一次我去办事,旁边有家书店,到里面看看,如果说能让你感动、有用的书几乎找不到。说起来有点狂。实际上就是这样。书无限多,但都平平。我拿起一本画集打开看,马上摇头,年轻人出这个书啊,拿到书号,给2万块钱,赶快出,我一天就能出一本书。
刘墨:这一点也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缺失大有关系。
石齐:文化素质的降低。
刘墨:但是当时吴昌硕也卖画,他的买主主要是在日本,日本人买画有个特殊要求,就是当他看好这一张画,就要求吴昌硕照着样子画100张,或者50张。
石齐:画了吗?
刘墨:画了。
石齐:吴昌硕某种因素是受任伯年影响,某种因素又受赵云壑影响。吴昌硕的文化基础,欣赏水平都在他们之上,诗也写得好,文章、字写的也好,修养也好,流露在画面上,吴昌硕来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大气、大家风范。
刘墨:所以我刚才问您,如何用概括的语言,概括一下中国绘画长处的时候,其实我很希望,您能提到一些,中国绘画除了视觉形式方面,这种样式之外,更多的是它的根基,它的根基在人的性情。
石齐:对,要说就在这一点上。我经常跟人说,别人还不承认。中国绘画只是“半个绘画”,你刚才说的这个题目,也符合了我的想法。它需要自己的学问起作用、情绪起作用,还要配上好诗词、好文章、好书法、好图章,这才组成一个中国绘画。你这些都拿掉,你这画就单调了。所以这些都拿掉,像西方的素描,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徐悲鸿的优点是造型,有贡献,极大弱点是把中国画品位弄低了,后面的一代代
的追随者集它的形,这幅画的形,中国画不是画形的问题,中国画是半个绘画,它需要很多修养。诗词、书法、图章、纸张是很讲究的,它形成一个特殊的体系。
刘墨:原来您说的“半个绘画”就是这么回事啊。我同意您的看法。您认为未来的中国画会怎样?
石齐:我们中国画搞的一定会比西方好,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中国艺术家很注意别人的优点,从他们的老祖宗一直到最现代派,我们研究又研究,用五十年的时光去研究,哎,这个大画家的祖先在哪里?你有什么秉性,你有什么代表作?用什么办法,我们了如指掌——非常熟悉。西方有这样的人吗?没有。我们的祖先这辈我们也研究,文化也重视,书法也重视,加起来如果搞的好,有才气,能比你差吗?这不是狂话。油画家们说这些人太狂了,我不理解,我说这两者都学了,再给它放出来,一定比单一的好,就像你瘸腿,人家两条腿,如果有才华的话,一定比他们强,这是我这么认为的。
刘墨: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展望。我在读历史的时候发现,文化复兴的周期一般是改朝换代后的70年,汉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都是如此。今天也不能例外,而且我自己也相信,大概再有二十年或者三十年,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各种秩序的越来越好,文化艺术和学术的顶峰,或者我们所期望的优秀的人,一定会出现的。
石齐:是的,一定会好的,西方比较乱,我们比较正,这也是优点。